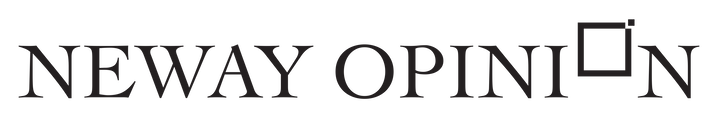文/卡尔
12月9日,香港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无意连任,震撼香港政坛。回顾他的任期,建制派和反对派大概都会承认,过去几年香港的管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然,梁振英和他的团队应该对此付多少责任是另一回事,笔者不予置评。接下来的特首选举,虽然选举的方式仍是“小圈子”,但可以明显感觉到舆论的热度远胜以往。因为中央在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的情况下,就决定下一届将任命新特首,此举给外界留了很大的讨论空间。各界的声音大都认为,下届特首的人选将会决定香港的治理路线。
对于下一届政府的治理路线到底会是“鹰派”或“鸽派”,相关分析文章已经太多了,所以笔者不会在本文具体探讨几位特首候选人和他们所代表的路线。可是,有个更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香港的治理最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定位是怎样的?
香港的治理目标,套用中央惯用的说法,四个字概括:繁荣稳定。接下来,就会导出三个结论:第一,香港被定位为一个经济城市。第二,经济好,政治才会稳定。第三,如果香港老百姓更多关心经济,不怎么关心政治,这被认为是好事。以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十月把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的典范加以肯定了,此举显然有敲打香港之意。
中央对特区政治的干预,并不是像很多反对派所强调的那样,终极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通过代理人的管制,慢慢蚕食香港人的自由。不如说,中央每一次出手,都是为了打压那些威胁到香港稳定的政治势力,最终是为了经济发展服务。同样的道理,只要为了香港政治的稳定,昨天的敌人也可以变成今天的朋友,正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爱国不分先后”。比如说,建制派内部就有大批像谭惠珠这样在过去亲英的人士。今年面对本土派崛起的新形势,张德江对素来反共的泛民主派递出了橄榄枝,表示泛民也是建制的一部分,回乡证也在最近解禁。张德江也表示,“乡土情怀,人皆有之。……但现在有极少数人,排斥一国、抗拒中央,甚至打出港独的旗号,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本土,而是以本土之名行分离之实。”注意,中央并没有否定“本土思潮”,只是反对借着本土思潮冲击香港现行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如果有一天现在的本土派人士放弃“港独”或“前途自决”的激进主张,在承认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保留香港本位的意识,也有可能在将来被吸纳进体制之中!
回到问题的核心,那就是香港的定位。根据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亚洲金融论坛上的说法:“未来,香港仍将义不容辞地继续担任连接者的角色,实现更好地把中国内地经济和世界各国经济对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角色定义地非常清楚:一方面要服务好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则要服务好全球金融市场。当大家来到香港时,其实来到的还是中国;但又能感觉到香港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优势。”他把香港未来的繁荣,寄托在成为“领先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金融中心”。
梁振英提出的这个远景,从经济上来说是可行的,当然这需要香港与中央政府的更多配合,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内交”的概念。问题在于,香港目前所有的优势,没有一样是将来内地的大城市不能取代的,比如内地近年来的自贸区战略,就让很多香港人看到了特殊地位遭遇挑战的事实。关键在于,如果繁荣稳定就是“一国两制”的全部目的,香港与其他中国城市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一天“一国两制”不能带来香港的经济繁荣了(世界上没有长盛不衰的经济体),或者换种说法,香港对于内地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一国两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最终在历史上会被定义为一个过渡期的权宜之计。
不久之前,“深港通”这种涉及香港发展的大事,完全被事关特首选举的新闻所遮盖。没人否认经济很重要,但是香港人在政治上的公民意识已经今非昔比。近几年来,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涉及到“一国两制”的前途。对于那些挑战《基本法》框架下的政治制度的激进“港独”势力,中央出于国家统一的原则当然要加以打击。然而,那些人所提出的论述和解决方案固然不可行,但抛出的问题是必须加以回应的。想要照搬过去的模式,把所有的问题斥之为“泛政治化”是不恰当的。香港人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和前途,也更多的关心政治,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央如果想要成功的治理香港,仅仅靠政治上间接干预不断吸纳新血,或者是打压威胁到体制的力量,都只是短期性的战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国两制”的意义何在,提出一个更大的论述。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邓小平在1984年的讲话: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他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方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这段讲话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然而,笔者要特别指出,很多人忽视了这段讲话中邓小平的视野,他不是仅仅把“一国两制”看成是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希望“一国两制”成为一种在世界上新的模式。
香港的 “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特区拥有比许多联邦制国家内部的州更大的主权(有学者把香港视为“次主权”的政治实体)。另一方面,特区所拥有的自治权又不是绝对的,中央在理论上也可以完全收回。而且,这不仅是分权,双方甚至还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央还承认了特区拥有特殊性,强调“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事实上改变了中国的国家性质,隐含着一个超越传统单一制民族国家的潜力——注意,这并不是说香港人是一个特殊民族,而是说这个制度可以超越世界上那种强调“特殊性”(分离主义)和强调“统一”(中央权威)的二元对立。即使在施行过程发现了不少新的问题,邓小平对于一国两制的设想,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实践,不能轻言放弃。
今天有很多香港人在思考“2047”这个问题。可是,反观内地,很少有人思考中国拥有香港这个特区的意义何在,还有“一国两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内地,关于香港的议题,似乎只有陆港矛盾的时候才会引起注意。这种状况很令人遗憾。在笔者看来,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另一层意义,是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野。最后,补充一段台湾学者赵刚论陈映真文学的话:
……台湾的长达半世纪的“殖民地经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藉由“殖民”作为一个中介所得到的对台湾人民与社会的理解,作为方法,进而建立一种比较贴近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的历史处境与文化状况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观点。也就是说,将这个“台湾经验”内在于中国的当代思想的起始感觉中,庶几可以建立一种比较坚实、比较内在的第三世界观点——可以更内在地理解韩国、越南、冲绳、印度,乃至非洲大陆。中国大陆在近几年的崛起中,在其周边所造成的疑虑,虽说和西方所进行的战略布局与利益动员有关,但反求诸己,中国大陆对周边“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缺乏同情的理解,也是原因之一罢。非洲太远就先不说了,就拿邻近的越南来说吧,我认为离开它近百多年来的殖民经验,以及长期在一个大国边缘的精神处境这两点,是无法真正理解它的,于是只能陷入一种对方是背信弃义的恼怒中。但现实上,这几十年来,特别是90年代后,大陆知识界的主要关心,在更乏道德意识的“追英赶美”的热症之下,已经不包括第三世界了,从而台湾作为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的这一特点,对其知识状况的参照作用,也就更难以被关注了,因为热症之下是不会停下来检查自己的知识状况的。
以上是就海峡两岸的知识界而言,如何藉将台湾的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不只是看成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同时也看成是一独特部分(即,“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开启重新理解世界和自身关系的契机而言。但是,对海峡两岸的知识界共同去把握一种“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观点”的最重要意义,可能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我们都知道,战后台湾社会因为不曾真正面对“前殖民地”历史,使得“中国(人)认同”在岛屿上陷入了不确定状态。陈映真1960年《乡村的教师》的主角吴锦翔,他认同他是中国人、他抗日、他认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如何成为左翼,而是如何成为“中国人”,因为他出生于1920年的台湾,并成长于皇民化的高潮时期……。这个“中国人”的意义与内涵,对他不确定、不自明,充满想像,而那固然是他不安与痛苦的来源,但同时也是一种更深刻的反省(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人”?)的契机。今天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有左翼有右翼,辩论争执都在“左”或“右”,但从没有提问:如何当一个中国(人)的左翼或右翼?这是因为,不知是好或坏,“中国(人)”是自明的。也许将来的台湾作为“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的视角,能够帮助在大陆的中国知识份子能重新思考“中国”。要将中国认同抽刀断水固然是虚无的、去历史的自毁之举,但将“中国”视为百分百完全自明,也未必一定是好事。“中国”需要在一种对其有“温情与敬意”的心情下,将之问题化。(赵刚《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
——香港的经验,又何尝不是如此?香港今天出现的激进本土派思潮,背后折射出全球性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崛起。中国必须勇敢的面对这一挑战。这远远超越一个城市的“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回应“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的体制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崛起的中国将借着这些讨论,开始学会如何面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珍视香港这片特殊的土地吧。